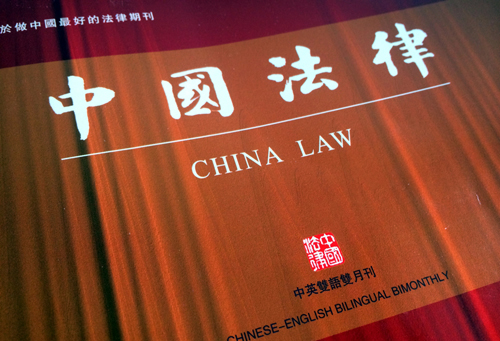谭某诉某广州科技有限公司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分析
关键点:职业病患者在工伤赔付前提下可否另行主张人身损害赔偿
案情概要
谭某于2005年入职某广州科技公司(下称“科技公司”)工作,双方签有书面劳动合同,最近一期劳动合同期限自2008年12月1日至2011年11月30日,该劳动合同第六点“劳动保护、劳动条件和职业危害”第(四)项对科技公司工厂车间作业时会接触的职业危害因素及危害性进行了知会,并要求谭某正确使用、维护职业病防护设备和个人劳动防护用品。2009年末,谭某参加公司年度体检时被检查出疑似职业病(矽肺病),随后科技公司即安排其进行进一步的诊断及治疗。为避免谭某再度接触职业危害因素,双方亦于2009年12月中进行了变更劳动合同工作岗位。
2010年6月,谭某经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诊断为矽肺壹期。2010年6月29日,广州市萝岗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作出《工伤认定决定书》,认定谭某在工作中受到的职业危害符合工伤认定的范围,确认为工伤。2010年11月1日,谭某经广州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为劳动功能障碍程度(伤残等级)七级。
2010年9月28日,谭某以人身损害赔偿为由向广州市萝岗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科技公司支付残疾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以及精神损失费等,共计人民币约18万元。
2010年11月11日,广州市萝岗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核发了谭某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2011年11月30日,双方劳动合同到期,科技公司与谭某终止了劳动合同关系,科技公司于同日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谭某支付了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终止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谭某收悉上述款项,并对数额没有异议。
本案经一审、二审审理,最终判决用人单位科技公司需向谭某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驳回谭某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观点:本案经一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法律适用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2条第一款规定“依法应当参加工伤保险统筹的用人单位的劳动者,因工伤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劳动者或者其近亲属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用人单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告知其按《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处理”。虽然《职业病防治法》第52条规定:“职业病病人除依法享有工伤社会保险外,依照有关民事法律,尚有获得赔偿的权利的,有权向用人单位提出赔偿要求”,但是《职业病防治法》于2002年5月1日起施行,而《工伤保险条例》和最高法《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施行时间均晚于《职业病防治法》。相对于一般性法律法规,《工伤保险条例》是属于新的规定和特别的规定,按新法优先于旧法的、特别法优先于一般性的原则,在处理劳动者人身损害赔偿案件时,应优先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本案中,谭某因职业病被认定为七级工伤,并依法享受了工伤保险的全部待遇,现依据《职业病防治法》的规定请求科技公司支付残疾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失费依据不足,不予支持。判决:驳回原告谭某的全部诉讼请求。
二审观点:二审法院认为《职业病防治法》第52条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2条第一款的规定之间并不矛盾,职业病人员在按《工伤保险保险》的规章享受工伤保险待遇后,若有工伤保险待遇中未包含的赔偿项目,而该项目依照有关民事法律尚有获得赔偿权利的,其仍可以要求用人单位予以赔偿。本案中,谭某所请求的残疾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均属残疾赔偿的性质,与工伤保险待遇中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性质相同,故不属于工伤保险待遇中未包含的项目。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工伤保险条例》对此并无规定,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及《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均对此作出了明确规定,对于该项目,二审法院予以支持。
综上,对谭某的上诉请求判决:一、撤销原审判决;二、科技公司于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五日内一次性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给谭某;三、驳回谭某其他诉讼请求。
固法律师评析
对于职业病患者是否有权提起民事赔偿权利,目前在广东各地法院、甚至全国各法院的实践均不统一。有的全部支持民事赔偿,也有的将职业病赔偿限于社会保险工伤赔偿,亦有的视为补充性赔偿处理。
由上述案例的判决可见,一审法院是按照民事赔偿与工伤保险待遇之间是唯一性的,职业病赔偿仅限于社会保险工伤补偿;二审法院判案则建立在职业病为工伤的基础上,在民事人身损害上的补充赔偿;对此,二审法院确定了职业病实行工伤保险和民事赔偿双重保障,但民事赔偿部分应扣除工伤赔偿已存在项目。
职业病补偿与人身损害民事赔偿能否同时兼得?对此,笔者较为倾向于同意二审法院观点。具体理由有如下:一、职业病患者提起民事赔偿部分依法有据。
2002年5月1生效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52条规定:职业病病人除依法享有工伤社会保险外,依照有关民事法律,尚有获得赔偿的权利的,有权向用人单位提出赔偿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48条规定,因生产安全事故受到损害的从业人员,除依法享有工伤社会保险外,依照有关民事法律尚有获得赔偿的权利的,有权向本单位提出赔偿要求。
就理论而言,职业病危害行为侵害的是劳动者的健康权或生命权,其实质上还是一种民事侵权。《民法通则》第98条规定,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第119条规定,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废者生活补助费等费用;造成死亡的,并应当支付丧葬费、死者生前扶养的人必要的生活费等费用。
结合《职业病防治法》、《安全生产法》、《工伤保险条例》以及《民法通则》的规定来分析,我们不难得出职业病赔偿权利人在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同时也可以要求用人单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此点从法律上有据可循。
二、职业病患者享受工伤待遇的同时提起民事赔偿从理论上可行。
因用人单位提供劳动条件具有危害性,侵权造成劳动者人身损害,导致劳动者受到职业病损害属于工伤,劳动者因工伤事故享有工伤保险赔偿请求权,因侵权享有人身损害赔偿请求权。二者存在于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之中,互不排斥。
(1)基于工伤事故的发生,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形成工伤保险赔偿关系。国家规定有较完善的工伤保险制度,目的是为了保障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职工获得医疗救治和经济补偿。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用人单位应当为本单位全体职工缴纳工伤保险费,因工伤事故受到人身损害的职工有权获得工伤保险赔偿、享受工伤待遇。因此,只要客观上被认定为工伤,就会在受伤职工和用人单位之间产生工伤保险赔偿关系。
(2)基于侵权事实的存在,受伤职工作为被侵权人,与侵权人之间形成侵权之债的法律关系,有权向侵权人主张人身损害赔偿。侵权之债成立与否,与被侵权人是否获得工伤保险赔偿无关,即使用人单位已经给予受伤职工工伤保险赔偿,也不能免除侵权人的赔偿责任。
三、职业病赔偿权利人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同时要求用人单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更有利于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体现保护弱势群体。
就职业病而言,其具有较为特殊的性质。职业病是一种终身职业疾病,患者会丧失劳动能力,一旦患有,通常情况下需要终身接受治疗,且病情会不断恶化,需要的各种费用也会不断增加,病变还有可能继续发展到死亡,将严重影响患者和家人的经济收入。如单单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由职业病患者享受工伤保险待遇,一旦双方劳动合同关系解除或终止,将可能使职业病患者将陷入重重经济危机,不但影响经济收入,更甚至无法再接受后续治疗、无法保障身心健康。职业病赔偿权利人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同时要求用人单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更有利于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体现保护弱势群体的立法精神。
四、职业病患者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同时要求用人单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该民事赔偿限于补充赔偿性质予以调整,符合公平公理原则,不会加重用人单位赔偿义务。
在职业病案件中,因用人单位具有双重主体身份——即工伤事故中的工伤赔偿义务人和人身侵权的侵权人。基于双重主体身份,劳动者有权向用人单位主张工伤保险赔偿,同时还有权向侵权人主张人身损害赔偿,但用人单位将基于同一行为或侵权事实承担双重赔偿的义务,并且工伤保险赔偿项目与人身损害赔偿项目的性质基本相当。在这种情形下,笔者认为,在用人单位已按工伤保险赔偿项目向劳动者承担工伤赔偿义务后,有必要对职业病患者向用人单位提出的民事人身损害赔偿部分予以限制。由此,在限制范围内由用人单位就工伤保险待遇以外的项目承担民事赔偿,才不会加重用人单位赔偿义务,亦符合“受害人不应因遭受侵害获得意外收益”这一基本法理及民法上的公平原则。
综上,笔者认为职业病侵权赔偿和工伤保险赔偿从理论及依据上均可以并行,但实行民事侵权赔偿与工伤赔偿双赔制度的同时,需充分考虑责任主体、权利人的身份竞合。职业病案件以工伤保险赔偿作为基础、民事赔偿作为补充的方式更能有效的保护权利人的合法权利,实现民法上真正的公平与正义,实现权利义务的真正对等。